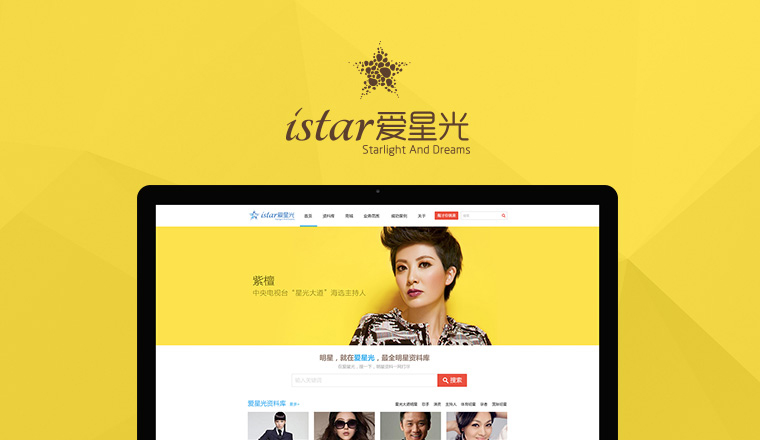关于「 互联网讨论消亡」的进一步思考
互联网讨论消亡,究竟是什么在逐渐消亡?这篇文章从“公共空间”和“对话”;两个关键词谈起,针对性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公共空间和对话方面的差异并溯源,发出对我国当前现状的感概。推荐对互联网、虚拟空间、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伙伴阅读
近三年前那篇旧文 《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 围绕了两个主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公共空间/领域”,一个是”对话”。2022年初受TEDxGuangzhou邀请,录了一段讲稿,当时的主题也是”对话”。
几年时间风云变幻,值得书写的公共事件层出不穷,我们(这个同温层内)的许多失望和愤怒的情绪或许依然可以归结在这两点: 一是“公共空间”,不论物理的还是虚拟的,实际上并没有对公共议题开放。人没有公开使用理性的空间。二是求“对话”而不得。
三年时间,移步换景。
环境在变,观察主体同样在变化:“讨论是否已经消亡”似乎都已经不值得问了。 这篇文章想要补充的是对“水土不服”问题的观察 。这也是此前的文章并没有覆盖到的 :溯源来看,“公共空间”和“对话”这两个概念的起源都是西方的。“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否正因如此,这两个概念才在国内这么拧巴、别扭、缺乏生存空间,甚至对一个巨大部分的人口来说难以理解甚至并不自然?
中国原生的社会组织形态被形容为一个如波纹推开的”差序格局”——”推己及人””一表三千里””治国齐家平天下”——家庭、家族、宗族、国家、天下,这些群组是一个逐渐扩大的范围,而 并不讲究从何处开始有了私密与公共之间明确的边界。
所以可以说,我们远了有家族(familial)空间,20世纪有集体(collective)空间,而公共(public)概念是外来的,且来了也不过一百多年。
曾经脱胎于西欧一整套政治哲学体系的所谓公共空间,到今天仍旧在这片东亚的土壤上发育不良。其中一个表征可能是 “既无真正的公共也无真正的私密” 的状态。公共对应着私密;公共空间的有意义的存在,必须建立在保证了私人空间同时存在的基础上。二者互相对照也互相支撑。
当我们说,缺乏一个可以自发、不受限制聚集,可以表达和讨论社会议题的公共空间,但其实反过来,不论在情感上、科技上、还是产权上, 我们也并不真正意义拥有不被侵犯的私人空间。 身体被侵犯,行为数据被挪用,家门被闯入。好像这种绝不可触碰、违背、僭越的边界意识,不论是概念的、法律的,还是空间的,始终没有成为不言自明的社会常俗。
父母进入子女房间,国家力量进入私家公寓,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可厚非,被视作礼仪问题或者文化问题,没必要上纲上线。这些可能都是西方”公共-私密二元关系”,与东方这套植根已久的流动、渐层式、人情为中心向外推开的空间关系相冲撞的结果。
©沙丘研究所
“对话”概念也在国内水土不服。 “对话”要求两个 平等独立的主体 。
这听起来如此简单,但在国内语境下面又是如此困难。如果平行浏览《理想国》和《论语》,那么回看同是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和春秋时期,苏格拉底和雅典的其他人谈话是一种来来回回的”掰扯”,他不停寻找对方论述里面的逻辑问题,然后试图用说理驳倒对方。这辩证(dialectic)是对话(dialogue)的基础。
但孔子不会和弟子有什么来回往复的“正题反题合题”,而是有人提问请教,继而孔子“答曰”。另外,孔子说出来的话就已经是最后的真理和最终的答案,记下来就好。这种交往形式的本质不同一直到现在都看得到明显的表征。
国内很多上年纪的人其实是没有“对话”的基本能力的,他们擅长的是识别尊卑、长幼、君臣、父子,知道面对一个权力比他高的人怎么说话,面对权力比他低的怎么说话,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一个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说话,特别是怎么样直接但又心平气和地表达不同意。
儒家的这种“家天下”传统也取消了所谓“个体”的概念。个体的存在需要一种“分离”,一种脱离于他人,脱离于人际网络的单独成立状态,“对话”也需要这样的两个个体。
但要是本来就黏在一起,本来就是“一家人”,哪要什么对话? 当家的想,小孩儿去国外读了书,现在回了家也想搞搞国外那套。有些家长乐呵呵配合一下,这配合来源于他知道小孩不可能真正挑战到他的地位。有些家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这好像在家庭或者更大尺度层面不断发生:年轻人想要的是和“家长”对话,“家长”想要的是作为年长者训训年轻人,年轻人觉得“家长”蛮不讲理,“家长”觉得年轻人不够依顺。
两边看似在互动,但实际上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没有在做同一件事。鸡同鸭讲,最后两边都气坏了。邓公有句话:“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
中肯的评价——我想,从150年前凸显出来就是这个问题,至今如此。只要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和西方那一套的本质上不兼容,更多纠缠难解的问题还会不断产生。但我没有浪漫化的倡导。“我们需要更多公共空间”“我们需要的是对话”——这样的呼吁还是太简单了,并没有回答水土不服的问题如何化解。
另一个需要补充的面向是:不管把问题叫做“讨论的消亡”、“公共空间的消亡”还是“对话的消亡”,当没有某个东西,我们就会倾向于浪漫化这个他者,理想化那个外部。 但其实那只是中文互联网中讨论消亡了,可以说这几年来全世界的互联网都在公共厕所化。
把三个所谓消亡放到墙外,几乎也一样适用,只是程度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彻底。这也当然不只是互联网的问题。欧美国家的骑士精神凋零,公共人衰落,极端右翼大行其道,撒泼耍浑者的谎话、拳打脚踢者的粗话、拍胸脯者的大话充塞着公共空间,偏偏就是没法好好说话。
回到国内语境,如果说这两个概念确是舶来品,那么比起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抵制的呼喊,我更好奇是否存在一种化解或者克服这种水土不服的方法。”怎么在中国做公共空间?“(或者“是否存在“是否可以这样称呼?)
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风靡过一时,因为它的萌芽;现在“公共空间”问题又流行起来,因为它的消失。 但这个问题意识的重新出现,好像并没有带来对它内生不兼容难题的细细剖解,我们在对它的使用上仍显含混。我一直认为虚拟世界的空间概念需要首先找到它在现实物理空间中的对应类型,否则这样的比喻缺乏依据。
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国内的“公共空间”常常被不加区分地等价于“外部空间”——建筑物之外剩余的部分,“绿地空间”——放绿植和喷泉的地方,“公众空间”——博物馆、画廊、展览馆,“社区空间”——仅对围墙小区内居民使用的活动场地……
建筑师、规划师小心地绕过这个概念内生的政治的部分,把“中国的公共空间”转译为在建筑和城市设计效果图里放上跑步、下象棋、跳广场舞的亚洲面孔,但这并不意味着找到了糅合的中途。 如果我们真诚地把空间问题辨识为总体问题的症结或者说表现,我想我们思考得还不够认真,或者说已经根本放弃了思考。
作者:陈飞樾;公众号:沙丘研究所
本文由 @沙丘研究所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 Unsplah,基于 CC0 协议。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给作者打赏,鼓励TA抓紧创作!
{{{path> 赞赏